每當政壇發生衝突,人們最常見的問題總是:這究竟是源自於人格特質,還是源自於政策立場?是意氣之爭,還是利益與理念之爭?是關乎感性還是理性?而通常,真正的答案都必須看到這幾個層次的結合:怎樣的政策問題,搭配上怎樣的人格特質,才導致衝突以特定的方式爆發?他們爭什麼,又為什麼是這樣爭?
在特朗普和馬斯克決裂的肥皂劇背後,故事正是由人格和政策所共同驅動。一直到四年前,馬斯克都還是民主黨人,在2020年大選中支持拜登。他後來之所以跟拜登鬧翻、轉投特朗普的陣營,與其說是為了純粹的商業利益,更是因為他在心理上認為自己過去沒有得到應有的「尊重」。而當馬斯克帶著鉅額資金投靠特朗普陣營時,特朗普對他也確實禮遇非常。
然而,在實際執政之後,面對種種現實上的政策問題、特別是各項政策背後的政治結盟考量,特朗普也無法再讓馬斯克享受這樣獨一無二的「尊重」。隨著馬斯克有意涉入的政策領域愈來愈多,在高科技的應用以外,更有意移民改革、政府財政等等問題,特朗普更不可能繼續充分「尊重」馬斯克的所作所為,容許馬斯克危及他對於政治結盟和政策運作的規劃。就此而言,在兩人的關係當中,特朗普反而是比較謹慎、穩重的一方。
不過,就在當地時間6月11日,分手一周的馬斯克又突然回過頭來向特朗普道歉,而特朗普也釋放了接納的意願。但從以上角度看來,恰恰反映的是形勢比人強。馬斯克並沒有他自己所想的那麼特殊,他不過是另一個高估自己實力、如果看不清政治複雜的現實、最終只會成為被君王拋棄的前任寵臣,如此而已。

比起馬斯克,拜登更尊重工會
這已經不是馬斯克第一次和他支持的總統鬧翻。
關於拜登與馬斯克兩人決裂的始末,普遍的說法是,拜登就任之後舉辦推廣電動車的活動,白宮邀請了幾大汽車製造商的高層到場,但身為電動車龍頭特斯拉的老闆的馬斯克卻並未受邀,讓馬斯克首度感到不被民主黨「尊重」。
拜登團隊的做法,其實也是出於政治結盟上的取捨:當時,汽車工人聯合工會(United Auto Workers,UAW)的工人正投入在近年最重要、最大規模的抗爭中,但有別於其他傳統大型製造商願意和UAW協商的做法,馬斯克的特斯拉根本不允許工人參與工會,特斯拉是美國唯一無工會運作的汽車大廠。從工會組織的角度來說,比起單次協商的成功或者失敗,封殺工會、排除工會參與才是最為嚴重的事情。
就此而言,即使不把馬斯克理解成UAW的頭號敵人,也不難理解拜登若在抗爭的緊要關頭與馬斯克同台,甚至大力稱讚他的貢獻、鼓勵他繼續擴廠增產,就是對工會運動的冒犯甚至背叛。事實上,UAW的幹部事後就向《華爾街日報》的記者表示:「我們並沒有發出最後通牒,白宮本來就理解。」
而工會的支持又是拜登得以當選的關鍵。畢竟,民主黨流失藍領階級白人勞工的支持,是一個長期的趨勢。在這樣的趨勢下,在密西根乃至威斯康辛等大選的關鍵州,獲得UAW這樣的大型工會組織的支持,是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的最後希望。因此,在馬斯克和UAW之間,拜登選擇更加「尊重」後者,背後的考量也就非常容易理解。
其實,單從商業利益的角度來說,馬斯克在拜登任內並未真正吃虧,反而獲大發利市:拜登政府任內大力推行電動車生產與消費補助,特斯拉是最主要的受益者,每台車的補助金額高達7,500美元,讓消費者能更無負擔地入手電動車;反而是共和黨右翼認為,綠能轉型是進步派陰謀,意欲除之而後快,在特朗普上任後就立刻著手刪除。另外,特斯拉也因為投資再生能源而獲得大筆聯邦補助,聯邦政策利好特斯拉,使得其他公司必須向其購買能源額度。
此外,拜登政府在太空、航空、國防等方面的投資,也讓馬斯克旗下企業承接的聯邦政府合同再創高峰,光是從NASA就獲得高達四十億美金的合約。雖然馬斯克在日後主導政治效能部時,不斷把「聯邦政府採購」描繪為「收買、浪費與控制的關係」,但從來,聯邦政府就不是馬斯克的敵人。對他旗下的多間企業而言,最大的買家本來就是聯邦政府,而即使是面向大眾的特斯拉電動車,銷售成長也都仰賴聯邦政府的消費補助。從拜登政府的角度來說,他們恐怕有理由認為,這樣實質的利益已經足以鞏固馬斯克的支持。

然而,馬斯克卻在愈來愈多領域都感到拜登政府的「不尊重」。到了2022年,當馬斯克再度無緣受邀與拜登同台推廣電動車後,他在推特發文痛罵拜登是「浸水的襪子玩偶」,這是他與拜登首次公開翻臉的紀錄,迫使白宮幕僚長親自致電安撫。
與此同時,拜登政府所任命的官員們也對馬斯克的商業帝國展開了幾波監管行動,包含聯邦貿易委員會調查推特是否違反用戶協議中的資料隱私條款(雖然這波調查早在馬斯克入主推特前就已經展開),司法部也調查特斯拉的聘僱歧視等等。加上民主黨進步派國會議員們討論開徵富豪稅,馬斯克又與跨性別女兒決裂,種種新仇舊恨,終於讓馬斯克成為民主黨的敵人。
在這個時候,在矽谷其他新右翼鉅子的牽線下,共和黨議員積極向馬斯克招手,對拜登政府的監管展開調查,新右翼網紅們更因為馬斯克「解禁」推特而對他讚譽有加,這才讓馬斯克徹底右轉。
在這個故事裏,決裂已經是感性與理性共同作用的結果:拜登的產業政策路線雖然大大有利於馬斯克的商業利益,但同樣的進步派經濟政策路線,也意味著更密切的工會結盟、更強力的法治監管。
偏偏,馬斯克的人格特質更加在乎「尊重」,此時,新右翼的網紅、共和黨的政治人物又願意給予馬斯克這樣的「尊重」。
政治成本巨大,特朗普無法繼續「尊重」馬斯克
到這次馬斯克與特朗普決裂,背後的道理其實相當類似:在執政以後,特朗普開始要做越來越多的抉擇。雖然他到最後關頭依然給足馬斯克面子,但馬斯克的「政府效能」計畫最終成為政治上的沉重負擔,根本未達到預期效益,特朗普必須緊急止血。相較於拜登選擇與工會結盟,特朗普則在關稅、財稅、科技等政策領域更顧及MAGA、新右翼的支持,也欲擴大與矽谷其他鉅子的連結,這些也都讓馬斯克愈來愈無法感受到「尊重」。
問題出在,馬斯克誤以為離開拜登後,自己就是特朗普的「唯一」,或者至少是「第一」,但他只是「之一」。
在所謂「政府效能」的問題上,馬斯克闖了大禍。他的強勢運作,令許多公家機關的雇員一夕失業,甚至一些專接聯邦政府訂單的企業、機構也隨之遭殃。這些人並不是新右翼政治修辭中不食人間煙火的高階官僚,而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是技術人員、文書處理人員,甚至是退役軍人,有許多甚至是特朗普的選民。馬斯克向這些人開刀,無疑會造成共和黨政治上的負擔。
4月,威斯康辛舉行最高法院法官選舉,被民主黨操作成對馬斯克的公投,而馬斯克也欣然應戰,投入大筆資金,結果他所支持的保守派法官大敗,令白宮敲起警鐘。

而在政府內部,馬斯克也與多名內閣部長發生了衝突,甚至在做出重大政策宣示時沒有告知白宮幕僚長Susie Wiles。這讓白宮必須有所抉擇。據多家媒體報導,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是馬斯克假政府效能部的名義,要求國防部向他提供對中國的軍事部署簡報,引起特朗普震怒,認為馬斯克撈過界,親自介入取消該場簡報。
另一個重要事件是,政府效能部越過部長們的頭頂,直接寄信給大批公務員,要求他們回信彙報自己工作的「五點價值」,引起多名部長向特朗普告御狀,最後這封信也沒了下文、不了了之。此外,馬斯克的部門「失手」開除了核子安全、航空安全的必要人力,又被迫緊急收回成命,又製造了混亂。
《大西洋雜誌》報導,馬斯克在內閣會議中嘗試挑戰國務卿盧比歐,質疑盧比歐縮減國務院人力的速度太慢;而盧比歐挺直腰桿,在特朗普面前表示他自有計畫,不需要讓馬斯克予取予求。有白宮幕僚表示,特朗普其實是從那個時候開始才對盧比歐另眼相看,認為他夠有膽識,而這也同樣佐證,馬斯克其實並沒有自己想像得那麼重要,不是特朗普心中的唯一。
至於馬斯克進入政府時宣稱自己可以大砍1兆的聯邦政府「浪費與貪腐」,但最後,也只做到了1,750億,達標率不到五分之一;而且,此一數字也被多名專家質疑大幅灌水,連在官方網站上都並未提供起碼的證據佐證,對於多筆採購合約的總價計算徹底錯誤。就連知名保守派智庫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研究人員都向記者表明,「政府目前所提供的財務資料,遠遠不足以支撐他們的宣稱」。同時,由於政府效能部所開除的雇員、所解除的契約當中有太多仍然涉及政府必要工作,政府之後很可能還是得要重新招聘、訓練相關人才,實際上很可能造成更大筆的花費。
由此可見,在政府內部和選民之間,馬斯克都已經帶來太大傷害。白宮有不具名官員向《華爾街日報》表示特朗普對此相當不悅,向幕僚抱怨「這難道全部根本就是一坨大便嗎?」(“Was it all bullshit”?)。而MAGA派的代表、特朗普策士班農(Steve Banon)也公開爆料,特朗普現在最倚重的財政部長Scott Bessent更是無法容忍馬斯克對財政的不負責任發言,在總統辦公室外大罵馬斯克是騙徒(fraud),馬斯克聞言用肩膀衝撞Bessent的肋骨,兩人發生肢體衝突,特朗普也表示「這太超過了」。
考量到馬斯克帶來的麻煩,特朗普還願意讓馬斯克「自願」卸任,已經是把面子做足,但馬斯克顯然無法接受。卸任背後是理性的政治考慮,但無法接受自己必須卸任,則是馬斯克的人格特質所致。

馬斯克無法接受自己不是「唯一」
除了政府效能部的問題之外,在其他政策領域上,馬斯克更發現自己頂多只是主子眼下的「之一」,很多政治決策不會以他為依歸。
在關稅問題上,據多家媒體報導,馬斯克對特朗普展開多次遊說,甚至還背著特朗普遊說企業大老,鼓吹他們也像特朗普進諫。但特朗普無意為他收回成命,是直到國債市場出現異常之後才終於轉彎。同時,馬斯克也在網路上公開痛罵原先主責高關稅政策的高階顧問Pete Navarro是「白癡」、「比一袋磚頭還笨」,凸顯特朗普核心團隊內部的分裂。
在移民議題上,希望多聘僱海外高階科技人才的矽谷右翼亦以馬斯克為實質領袖,與希望縮減所有移民的新民族主義者、MAGA核心圈策士發生衝突,在特朗普上任之前就對H1-B簽證問題爭執不休;在那波衝突中,馬斯克獲得暫時的勝利,但也是經過一番爭取才終於成功。事實上,此次的預算法案成為馬斯克與特朗普衝突的導火線,馬斯克抨擊法案下政府支出過度膨脹,但特朗普政府就增加支出,有超過1,500億美金花在打擊移民的各種措施之上。
而在科技領域,情勢則彷彿拜登電動車事件的翻版。馬斯克不滿其他同業也能獲得特朗普的垂青,而特朗普並不想為了馬斯克而將其他科技鉅子拒於門外——尤其當其他人的產品比馬斯克還要成熟的時候。
《華爾街日報》報導,馬斯克的仇敵、OpenAI創辦人奧特曼已和特朗普政府達成協議,要共同在阿聯酋針對AI運算展開合作,計畫名稱為Stargate UAE。為了此一計畫,特朗普要親自到阿布札比和奧特曼同台,稱讚他的貢獻,並在從美國到阿布札比的航程中與奧特曼面談。馬斯克自己旗下的xAI技術發展則仍遠遠落後OpenAI,無法與之競爭,但他依然為此大為火光,向白宮表達不滿,為此,合作協議延遲一個禮拜才終於正式宣布,同台公開活動也被取消。
表面上看,這也像是馬斯克的勝利,但也佐證了四年過去後,馬斯克依然無法接受總統對他的競爭者投以關愛的眼神,而這樣的索求自然也不利於關係的長期經營。何況,馬斯克只爭取到同台活動取消,卻無力阻止特朗普在AI領域繼續與OpenAI合作。

與此同時,亞馬遜的老闆貝佐斯也多次向特朗普輸誠,包含強勢阻擋自己旗下的《華盛頓郵報》在選舉中支持賀錦麗;而貝佐斯的火箭公司BlueOrigin雖然尚不如馬斯克的SpaceX成熟,但也希望能獲得更多聯邦政府契約,不讓SpaceX獨吞這200億美金的聯邦訂單。在這些領域,聯邦政府是最重要、甚至唯一重要的買方;馬斯克眼下雖在技術面握有優勢,但日後的競爭在所難免。在這樣的情況下,一般的紅頂商人可能會選擇認命,知道自己必須與其他人競爭,因此更努力經營與特朗普的關係——但這不是馬斯克的選擇,他的人格特質不允許他這麼做。
而這個人格特質恐怕對他的政治影響力毫無幫助:和一位總統鬧翻或許只是運氣不好,但能和兩位總統鬧翻,只能說是馬斯克太過高估自己。畢竟,政治實在太過複雜,從來都涉及太多利益的交換、太多不同部門的協商,特朗普再怎麼倚重馬斯克,都不可能只以馬斯克為依歸。在這個時候,至今最準確的回應可能並非來自美國,而是來自歐洲:在三個月前,馬斯克意氣風發,在推特上訓斥波蘭的外交部長「閉嘴,小男人」;三個月後,這位外交部長終於逮到機會反唇相譏:「看吧,大男人,政治比你想像得更加困難。」
復合?為什麼而結盟,能維持多久?
僅僅一個禮拜之後,6月11日,馬斯克就公開表示他的一些推文「太過火」(went too far),因而感到懊悔(regret);當日,特朗普親自告訴《紐約郵報》記者「我認為他這樣做是很好的」(”I thought it was very nice that he did that.”),言下之意是接受馬斯克釋出的撤退訊號。在這個過程中,特朗普在面子和裏子上都並未有任何有意義的讓步。馬斯克以為自己手上的牌足以支持他押上大量籌碼,翻牌之後才發現自己凶多吉少,只能怪自己太晚明白這項道理。認錯求情,是希望能夠「投降輸一半」。
在此之後,原先重貶15%的特斯拉股價終於止跌,重新上漲逾2%。這也再度佐證,即使在投資人眼中,馬斯克當前的實力在相當程度上取決於他和特朗普的好關係。特朗普可以只把馬斯克視為「之一」,反倒是馬斯克必須將特朗普看作「第一」。
值得補充的是,6月11日這樣的交手可能只是公開和解的一個下台階,而幕後可能早已策劃多日:根據CNN獨家報導,其實早在6月6日,副總統凡斯已經請示特朗普希望如何處理,特朗普指示要「具外交手腕的」(diplomatically,延伸意指委婉、和緩、留面子的處理方式)應對,於是凡斯偕同白宮幕僚長兩人與馬斯克通話;接著,6月9日,特朗普和馬斯克兩人已經先行透過電話會談。之後,針對特朗普派兵前往洛杉磯,馬斯克亦發文表態支持,亦在推特上重新追蹤白宮的副幕僚長。不難發現,整個過程中,主動權幾乎全在白宮手上。
假使馬斯克當時只是威脅翻臉,白宮可能還會為了拉攏他而多給一些甜頭,就如同特朗普幕僚最終並未讓特朗普與奧特曼同台,恰恰是為了安撫馬斯克。但是,在馬斯克發瘋翻臉之後,不論是針對科技、移民、財稅等各個面向,又或者是針對政府人事任命問題,他都失去了話事權,相當於什麼都沒有要到。

馬斯克也被迫面對自己政治實力的限度:雖然他在推特上警告共和黨一眾國會議員,表示特朗普只能再做三年,他自己則還會在圈內待上許久。但是,在預算法案這個他自己所選擇的戰場上,除了先前早已反對此一版本法案的極少數議員外,其他任何議員都並未響應馬斯克的召喚,頂多表示希望兩人重修舊好。背後道理也很簡單:得先活過這三年,才能思考未來三十年。特朗普在共和黨上上下下都有難以撼動的控制能力,而沒有任何共和黨議員想在這時候得罪特朗普,遑論附和特朗普最新的仇敵。
眾議院議長Mike Johnson的警告無比清楚:「跟你說吧,對美國總統,你最好不要質疑、不要自以為高明、絕對不要挑戰。」甚至有分析者認為,馬斯克的表態反而讓預算法案更容易順利通過,因為共和黨議員即使對法案有意見,現在也不願被認為是陣前倒戈,被看做是在特朗普和馬斯克之間選擇後者。
他只能慶幸,自己的金錢與社群媒體實力依然有利用價值,他背後的矽谷鉅子網絡亦如是,包含Bill Ackerman等金主都表態希望兩人和解,所以特朗普願意和平解決,否則依照特朗普的為人,馬斯克恐怕得做出更壞的打算。
畢竟,對馬斯克而言,此刻的情景與兩三年前差異實在太大。在兩三年前,當馬斯克與民主黨翻臉時,新右翼社群與共和黨議員立刻補上空缺,盛讚馬斯克,對他禮遇備至,歡迎馬斯克來到他新的歸宿,而特朗普更是倒屣相迎,讓馬斯克成為極少數能和特朗普分享鎂光燈的人物。但此刻,當馬斯克脫離MAGA的圈子,他就什麼都不是,除了政治實力低落的少數人(如Andrew Yang、即楊安澤)以外,根本沒有人願意接納他,遑論迎接他成為新的霸主。
他和自由派的橋樑已經燒斷,甚至是頭號公敵;從民調上看來,對他仍有好感的民眾幾乎全是特朗普的支持者。若他和當前特朗普領導的共和黨也徹底翻臉,那麼就如同他的政敵班農對他的譏嘲,他將成為政治上的「無國籍者」,或者說就只是一名浪人。
而特朗普不是拜登,早已證明他會用聯邦政府的力量打擊仇敵,絕對不會猶豫,即使損及既定政策目標也會毫不保留。恐怕任何稍稍理解美國政治的人恐怕都知道:就算惹得起拜登,也不代表惹得起特朗普。
對此,政治專業媒體Politico召集旗下15位經營不同政策領域的記者,即時分析多項特朗普可以懲罰馬斯克的具體方式:

交通部可以阻緩核准特斯拉的自動駕駛新技術,甚至主動展開多項安全性調查,並加嚴既有的安全檢測;民航局可以拒絕讓SpaceX的火箭升空;目前美國政府的國防和太空政策的確仰賴SpaceX,雖然貝佐斯等人的企業尚且不夠成熟,無法立刻取代SpaceX,但特朗普也可能選擇在國際航空站議題上重新找俄羅斯合作,在新的國防計畫中更可以多給傳統軍事工業和矽谷新興企業機會;商業部可以讓馬斯克的Starlink拿不到聯邦政府網路建設的訂單;馬斯克投資的腦神經工程本來就涉及高度管制的領域,具有相當的健康風險和倫理爭議,食藥署可以讓他試圖涉足生醫產業的Neuralink計畫胎死腹中。甚至,馬斯克的xAI相當耗費電力,也在曼菲斯當地造成嚴重污染,環保署至今仍拒絕調查,但只要環保署改變主意,馬斯克的AI公司就可能面臨斷電危機。
劃下楚河漢界之後,馬斯克才愕然發現自己能控制的範圍遠比他想像中得小,縱然有拔山蓋世的自傲,最後也只能徒呼負負。
從民主黨到共和黨,馬斯克把來自聯邦政府的幫助甚至保護視為理所當然,更忘記自己的產業高度仰賴聯邦政府的訂單,除了聯邦政府之外其實沒有任何的買主。這些投資與保護遠比電動車產業是否能持續得到補助更為重要,不僅僅是銷量多寡的問題,而是涉及公司是否能持續營運的根本關鍵。
誠然,聯邦政府依然需要馬斯克旗下企業,但倘若魚死網破,聯邦政府的幾項政策只是破掉的網,死的依然是馬斯克這一尾大魚。
而海裡總還有其他的魚。即使心理上再怎麼無法接受,經過這個禮拜,馬斯克或許總之明白了,在各種複雜的政治現實中,他不是特朗普的唯一,也未必總能夠搶到第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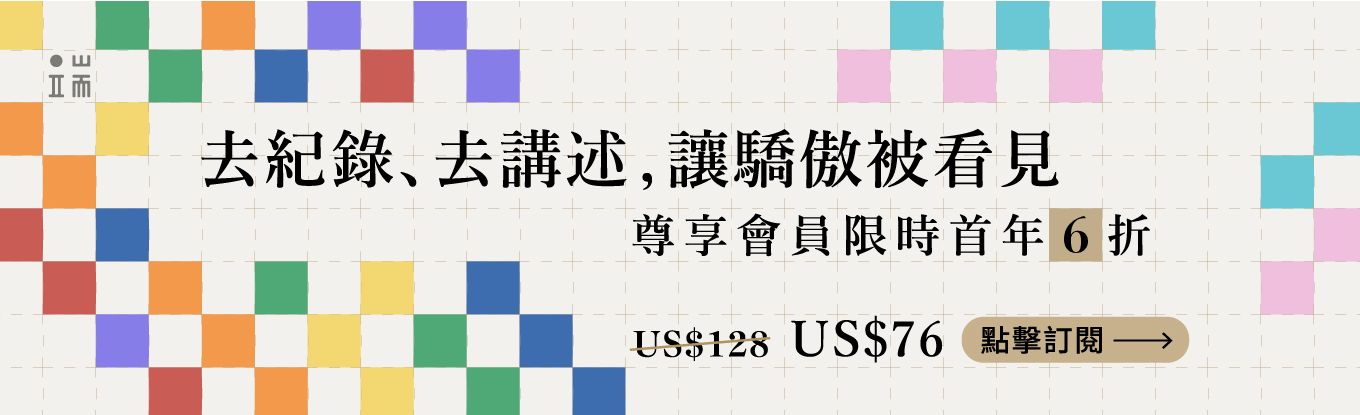



評論區 0